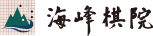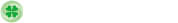2025.07.15| 媒體報導
2025/07/15【棋編碎碎念:能不能好好說再見?】

圍棋史上最著名的樵夫當屬王質,其傳說廣為流傳,有趣的是,王質最早的職業不是樵夫,而是一名道士,出自西晉司馬彪所著的「郡國志」:
「昔有道士王質,負斧入山,采桐為琴,遇赤松與安期先生棋,而斧柯爛」
意指道士王質上山,遇上兩位先生下棋;文中「赤松子」和「安期生」皆是古代傳說中的仙人,王質觀棋,看著看著,上山攜帶的斧頭,其斧柄竟然腐爛,可見時間跨度之大。
這則故事到了東晉虞喜所著的「志林」,不但王質爬得山有了名字,叫「信安山」,場景也多出描述,成一間石室,下棋的兩位先生則變成兩名童子;而王質這次觀完棋,還有機會回到家中看一看,發現「鄉里已非矣」,刻畫出滄海桑田、人事已非的愴然。
王質身份的轉變相信在文學創作中是有原因的,畢竟一名道士的志業是升仙求道,能上山巧遇兩名仙人,簡直是求之不得的事情,巴不得趕緊磕頭拜師,立即修習成仙之道,多了幾分成全,就少了那麼一點悲壯,用樵夫作為主角更貼近凡夫俗子,也更能代表芸芸眾生。
等到南朝梁的「述異記」,也是後世最經常流傳的版本,故事還企圖讓情節變得更合理一些:像是王質為什麼會被棋局所吸引呢?一名平凡的樵夫豈能參透神仙之局?原因是童子一邊下棋,還一邊唱歌,王質是被童子的天籟歌聲所擄獲,這裡神似魅惑的吹笛人。
至於王質為什麼能跟著神仙童子活上上百年,等到斧柄腐爛都不會變老呢?那是因為童子送給王質吃棗核,應該是某種仙丹靈藥。
此外,於述異記中,王質不是自己發現時光流逝的,而是童子向他發出警告:「童子謂曰:『何不去!』」王質才驚覺斧柄已爛,趕快下山回家,結果「既歸,無復時人。」
仙人的出口喝斥,讓王質的逗留多出執迷不悟的情緒在裡頭。
後來流傳的故事版本大同小異,仙人或童子不是唱歌,就是下棋,而王質總歸是羊入虎口,慕聲而來/慕棋而來,最終穿越時空,人事全非。
有人說,這是一則成仙的故事,王質在觀棋過程中領悟仙道,跟著仙人的腳步成仙了;也有人說,這是一則警世故事,棋局被比喻做爭權奪利的人間,只有神仙才看得懂,王質妄想懂,花費一輩子沈浸其中,結果物移星轉,轉瞬人生。
不過,每回聽王質爛柯的故事,我總是感到無可名狀的哀傷:他怎麼就不能有機會好好說再見呢?
初學圍棋之際,少有對手過招,手指頭數得出來的面棋,是同學的父親;這位叔叔看上去聰明睿智,據說是國內大企業退下來的高階主管,攜家帶眷移民,遷至遙遠北國,堪稱現代版的隱世高人。
叔叔的興趣除了收集電影DVD,還喜好下棋,雖然只有級位棋力,但已夠折騰我這名初學者;每每周末到同學家玩,一老一少總得糾纏一盤棋——正面交鋒、你爭我搶、爾虞我詐、纏繞攻擊、七出祁山之後,才能繼續當天的其他行程。若說叔叔是我的圍棋啟蒙也不為過。
然而,畢竟拳怕少壯、棋也怕少壯,我下棋過癡,不務課業,棋力突飛猛進,叔叔日漸下得吃力;升學前夕,我棋力晉段,叔叔已無招架之力,但我們每次見面還是會以棋會友。
被指導的學生變作老師,格外彆扭。我雖處處退讓,但放水痕跡太過明顯,叔叔愈下愈不來勁,最後棋無關勝負、無關緊要,如同閒話家常,不起波瀾。
上了大學,開啟全新的視野,直通花花世界、五彩繽紛;成天都在忙,忙著看、忙著玩、忙著戀愛,就是沒忙著讀書;青春的日子不夠用,沒時間想起高中同學,更沒時間想起叔叔。
一轉眼,大學畢業了、研究所登出、面試完第一份工作,矇矇懂懂、渾渾噩噩,生活種種像踩了油門,等回過神來踩煞車,叔叔的訃聞已是幾年前的事,聽說是肺癌。
沒來得及道別,連幸與不幸都是聽說,王質不也是如此?
前幾年,大疫方過,同學在台北舉辦婚禮,步入人生的下個階段;家長席上留了張空位給被迫缺席的父親。我瞧著走在紅毯上的同學和另一半,想起叔叔在天之靈,一定正在微笑吧。
怪哉,資訊四通八達,被無線網路縮小的世界,我們活得如此擁擠,卻又如此疏離。
愈來愈多趕不上的再見,總是猝不及防。在這個埋頭苦活的社會,誰說我們不是現代王質,你也是,我也是。有時,也說不上來是誰把誰給遺忘。